|
拾柴 2012年秋末的一个周末,回老家看望父母。 闲暇之余,到东山帮哥哥刨地瓜。既算帮忙,也是重温故事。 山坡路边成片的草荆刹是茂盛,快有我高,泛黄的荆棵秋风中摇弋,发出“沙沙”声。在一些电影中能够看到类似景象。这,勾起我的回忆。 哎,想当年哪有这些,不等荆棵长高,早早的就被乡亲们收拾回家当柴禾了。 那年头,没有哪家能买得起煤炭,家家都靠烧柴做饭。 每年秋季,各家各户想尽办法,收集各种能烧的东西,以备整个冬季使用。 我家也不例外。母亲会催促我出去拾柴禾,尽管自己很懒,很不情愿,但在母亲的责备催促下,还是经常外出拾柴。况且,那时隐约感觉到:生计重要,这是我应做的。所以,有时也主动约上伙伴,去到野外。 那时没有什么“除草剂”,秋天里野草生长的很快,玉米地的垄沟里全是绿荧荧的杂草。 一些人家拔草晒干后喂牲口或兔子,我弄回家当火头烧。 钻进玉米地,找到野草的根茎位置,抓住后用力上提,好大一把草就被拔离土地,甩掉泥土,攒到够一抱后就抱到地边的堰上。 干这个活要受点小罪。玉米叶跟锉刀似的,划得我身上一道道红痕,厉害了还会冒出血来。虽然是秋天,但玉米地里还是象蒸笼似的既闷又热,汗水浸在伤口上生痛。但受不得罪得不到绿草。 秋后,庄稼已经收获完毕,成捆的玉米秸已收集到生产队的场院里,留作耕牛的食料,但田地里还会有残留。我左手将大的秸叶拣拾起来,放到右臂掖下,累积到“一夹哈”(即掖下已塞满了),就放到柴堆上。 时不长还能拣拾到成段的玉米秸,烧起来比秸叶出数。一把秸叶一把火就燎完了,但秸杆能燃烧较长时间。 感觉已经够量,就将绳子顺在地上,再把玉米秸叶一抱抱地放在上面,用力捆扎,系成活扣。将柴捆提到一边,再将遗漏的秸杆插到柴捆里。 提着绳子用力背在肩上,感觉一下背后的柴捆是否左右平衡,如果“偏沉”,就要放下重新捆扎。 玉米秸没的拾了,就刨玉米秸的根,我们叫它“棒子茬”。 抡起小镐头,使劲将“棒子茬”掘出来,在地上将泥土摔打干净,放置成堆。运回家后,平摊在家的院子里晾晒,打眼看“棒子茬”的形状很象鱿鱼——现在看来。 收集枯草要有工具,即耙子。家里有把耙子,但材料是竹片做的,既不结实也不好用。伙伴们有使用钢丝耙子,它比竹耙子更上柴火,即收获会更多。我也一直想拥有一把钢丝的,这样拾得柴禾才不致以落后伙伴。在我不懈要求下,母亲终于从集上给我购买了一把。 手握耙子柄,肩跨柳条筐,直奔草场——东山。 选择野草厚实的山坡,开始搂柴禾。 耙子放在身后,柄头置于肩上,双手背着用力压住耙柄中间,一味向前走就是。不一会,野草就沾满耙子。将耙头背过来,使劲在地上撮,就能将野草从耙头退下来。 不一会,各种枯草的茎叶就堆成大堆,不过是虚藤的,要一撮撮地压实,才可装在筐中,不然,在路上会散架的,我们叫“窝漏”。 伙伴们比试谁装得筐大,说明谁搂得柴多,最大的叫“辕筐”,意思是没有再大的了。 有时,我们一帮伙伴结伙到“地下话”(即解放军挖的防空洞),那里有很多杨树,秋风会把杨叶吹落。我们一边游玩,一边“穿杨叶”。 每个伙伴都拿一根粗铁丝,后面栓上长长的麻绳,绳子尾部栓根枝条做挡头。看到大的杨叶,照准其中心穿下去,攒到厚厚的一摞,再撸到麻绳上。不多时,身后的麻绳就累积了好长的一串,这时拖拽也困难了,就将挡头解开,将杨叶全撸下来。 怎么运回家呢?不是问题,我准备有麻袋呢。 将袋中的杨叶按压结实,背在肩上,晃晃悠悠往家走,这是因为杨叶还没干透,重呀! 夏季,也有柴禾可拾,就是刨“麦茬“。 收割完小麦后,生产队的社员将麦穗和麦茎运回到场院里,麦茎的根就不要了。 它也是上好烧火材料。象刨“棒子茬”似的,顺着田垅向前刨,觉得够数了,一并去土、装筐。 “劳动”结束后,手上磨出硷来是肯定的,有时还磨出水疱。 村里的成年人还到山上割荆棘当柴烧,它是木质,在我们这个缺少木柴的地方,算是上等的柴料了。但我没割过,也不想尝试去割。一是它们生长在崖壁上,我害怕滑落;再就是,它满身针刺,你能保证不被扎到?我怕疼。 我拾来的柴火,都集中在家里的“驴棚”里,能垛到一人多高。每次“劳动”回来,能得到母亲的夸奖。我欣慰,我骄傲。 有了足够的柴草,母亲就不会发愁了,就能放心地为全家人烧火摊煎饼了。 2012年11月14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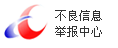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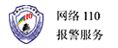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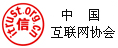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