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深圳漂泊了十年,终于回到了北方的家乡。十年来,一直无法适应这个南方城市的生活,感情无所寄托,事业上也没有任何发展。性格不爱打拼,人生自然暗淡。但尽管如此,我却完成了我们家的一件大事,我找到了失踪二十多年的小姑,并把她带回来,埋到了祖父母的身旁。祖父母生前曾一次又一次地对家人念叨:“不要忘记英子呀,一定把她找回来呀!”英子是小姑的名字,年轻时因对婚姻不满而离家出走,一直杳无音讯。现在,我终于把她找了回来,完成了祖父母的遗愿。如果祖父母泉下有灵,也该心安了。 二十五年前,我七岁,小姑二十一岁。秋收后镇上开物资交流大会,各村的人都去赶会。小姑跟人去赶会,什么东西也不买,只看歌舞团的演出。上午看了,下午还看。傍晚回来,便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演出的情况,说港台歌曲如何好听,迪斯科舞如何好看。当时家乡人把迪斯科舞讥讽为扭屁股舞,见小姑讲得起劲,爷爷便斥责她说:“小闺女家家的,不知道羞耻,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回来说!” 物资交流会一共五天,到了最后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我早早起来,就缠着小姑,非要跟她去赶会。小姑不愿带我,我就哭哭啼啼,抓着她的衣服不撒手。奶奶也帮我说话。小姑没办法,只得带我去。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镇上,因为是最后一天,各摊位上都在喊着:“大减价了!大甩卖了!”小姑也不理会,领着我径直走到歌舞团演出的地方,一个用红布围起来的场子。小姑买了两张票,我们就进去了。舞台上有人敲着锣,指挥猴子翻跟头,我便着急地说:“小姑,咱来晚了!”小姑说:“这不是正式演出,是招引人的。”果然,看了半天猴子翻跟头,正式节目才开始。这是个南方的歌舞团,演员穿着鲜艳夺目的服装,说话叽里咕噜的,幸好唱歌用的是普通话。演到后半段,开始跳迪斯科,男男女女站满了舞台,一齐扭屁股。领舞的是一个小伙子,下身穿着白色紧身裤,上身穿着花条衬衣,爆炸头,蛤蟆镜,一边扭屁股,一边向观众抛飞吻。人们都大叫起来,小姑也尖叫着向他招手。舞蹈结束,小姑便掀起活动的幕布,钻进了后台,一会出来,递给我两块钱说:“庆子,你一直往东走,供销社那里有炸油条的,你去买二斤,咱们回家路上饿了吃。”我不敢推辞,便拿着钱往东走。过了供销社,一直走到镇外,也没看到有炸油条的。又走回来,问供销社的人,人家说:“都快晌午了,油条早卖完了。”我便赶紧往回走,到了歌舞团演出的地方,发现幕布已经撤掉,演员们正在拆卸舞台,往一辆大卡车上装。台下场地上,观众全部散去,小姑也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下子恐慌起来,一边大声叫着小姑,一边朝四周张望。叫了半天,也没见小姑的影子。我怕小姑回来找不到我,便在原地等着,不敢挪窝。直到歌舞团把舞台拆完,全部装上汽车开走了,小姑也没回来。 空荡荡的场地上只剩了我一个人,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起来。会上做买卖的摊位已所剩无几,地上到处是烂菜叶、水果皮和碎纸屑。就在我惊恐无措之时,碰到村里一个开着拖拉机卖煤的,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便把和小姑走散的事告诉他。他安慰我说:“别害怕,孩子,你小姑可能有别的事,先回家了,你跟我的拖拉机回去吧!”听了他的话,我才不害怕了,便坐着他的拖拉机回到村里。但回家一问,小姑根本没回来。奶奶先慌了,赶忙对父亲和叔叔说:“英子看来是跑了,你们快去找找她吧!”爷爷却气得跺脚道:“别管她,看她能跑到哪里去!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来!”听奶奶和爷爷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们对小姑的失踪,已经早有预感。我开始后悔起来,如果我不听小姑的话,不去买油条,一直跟着她,她就走不了。我觉得是我把小姑弄丢了。 过了十几天,小姑的对象家听说了这事,便来要人。爷爷觉得很伤颜面,本来两家已经商定年底结婚的,小姑跑了,只得把彩礼归还人家,还得陪上很多好话。小姑那个对象已经找了好几年,是个挖煤的,挣钱不少,人也很老实。每年他都来家里好几次,小姑一直不冷不热,好像对他不太满意。我虽然才六七岁,但懵懵懂懂的,已略知风月。我看到小姑天天把头发挽来挽去的,后面扎着块白手绢,每次出门,都要在镜子前照一番,走到哪里,身上都带着一股雪花膏的香味。而她那个对象,每次来了,都是扣脖严领,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我心里常常感到不平,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得上小姑呢。但没想到的是,小姑却选择了逃婚。从此,只要一听说谁要出远门,奶奶就托人家打听小姑的消息。刚开始,爷爷总是没好气地说:“找她干什么?死在外头算了!”过了一段时间,也不再说这样的话了。有时候,爷爷还写了寻人启示,偷偷跑到县城里张贴。后来,爷爷便跟着一个工程队出去干活,快六十的人了,天南地北地跑,就是为了寻找小姑。我上高中的时候,爷爷去世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奶奶去世了,他们都没能见小姑最后一面。(待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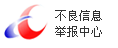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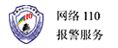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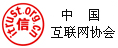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