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法和文章、绘画 世上只有汉民族的文字可以写成艺术,原因有二:它是象形文字,它用毛笔书写。如果还要研究,应该与这个民族曾经拥有而今却淡化了的追求精致的心理有关。 先贤们为我们留下了风格迥异的书法作品,很多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居延汉简、敦煌文化典籍中书法之精,据说超过了当时的颜柳等大家。印刷术虽是我们祖宗的发明,但在“唐人尚为盛为之”的时代,这些浩帜都只能是一笔一划的书写。一人之力骤难完成,必是多人协同,夜以继日,以虔诚之心历经几代、十几代的工程。期间不乏皓首穷经、呕心沥血的组织者。但今天我们欣赏这些瑰宝时知道谁的名字?就连组织者也寂寂于灿烂文化中,构成辉煌大业一分子,他们为中华民族文化又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一朵奇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为什么书法特别强调临摹功夫?为什么现在要大力反对“丑书”?原因很简单:我们比不上古人!那些自以为创新,自以为反映了时代风格的白纸黑字,不过是把这个时代最该克服的劣性——浮躁——表现在书法里了。这与历代传承的书法精髓——精致高贵、炼心炼性是背道而驰!学书者于此不可不察,不可不慎。 书法是载文的,丑书是畸形的艺术,与缠足好有一比。脚是走路的,缠足是变态的审美。从本质上讲,丑书与缠足意义相同,不过缠足痛苦血腥,外人看不到。缠足成功则风摆杨柳、婀娜之状顿生,给我等色鬼饱以眼福,但到中老年后则颤颤危危,几成行将就木的骷髅。丑书却要立刻见人,拿出炫耀时看似任性挥洒赏心悦目,小则叫卖于集市,大则能金钱铺路,登堂入室,鉴定成万亿之价,让我等“书盲”羡慕嫉妒恨迸出。实则毫无根基,不值大家一哂。书法习练能静心醒目、强身健体,但却是要先有一个煎熬身心的过程,达到有章有法,才能以意使笔,挥洒自如,丑书缺少的正是扎实的功底,怎能有长久活力? 文以载道——道就是思想,才是最珍贵的东西。此处的“文”,是广义的散文,似诸子百家、唐宋八大家及之后的公安、桐城派等散文。文为载体,也就是有后勤保障的功勋。读圣贤书有启发而做文,此即为文之道。古代文人往往拉大旗作虎皮,明明是自己思想却说是“代圣人言”。体现读与文的就是书法,是知识分子的本能。 文以载道,常会被人利用,其形式也是上层建筑之一,会变成某种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非作者思考的载体。明清时代的八股文(今人往往误解成明清科举只做八股文,其实还有很实质的东西。八股文只是科举的一门课,没实际意义,考中即弃之不用,只有礼部出题人当做宝贝。就像现在各级各类的外语考试,费尽心力过关大多数人没什么用处,只有外交学院的那帮洋奴奉为至宝),只是一时代的特色,最终与“道”背离越来越远遭到抛弃。古时“润泽鸿业”,近代“为什么服务”提法,正是文章得以永存的灵魂。有人说“为什么服务”的提法给文学造成戕害,应吸取教训,不得再提,应倡导人性化。其实“为什么服务”就是自古以来一直提倡的“为时而作”的大白话,古今中外的所有文章“为时而作”是永恒真理。诸子百家也是处于变革时代而产生的新思想,当时有直接体现民生的墨家农家之说,有以建新政弥乱世的法家儒家兵家之说,有讥不平而无奈何的道家名家之说;两汉大赋反映了中国最强盛王朝的雄雄大气,;六朝韵文正是养尊处优顶层士族生活的体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不打上时代烙印;近代“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新文化”运动的“以我手写我口”也是为自己的阶级服务的;现在大V们倡导的“人性说”、“普世说”更是赤裸裸的打着“人”的幌子为自己的利益集团服务。他们沦为自己阶层的利用工具,都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只有毛爷终生号召的“为工农兵服务”,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为文离不开自己代表的阶级,都是“为什么服务”的,只有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服务之分,若能脱离现实,那只有遁入地狱。然空门不空,无所遁也。 练书法者可以在墨池隐居,以求独善其身,倘若痴迷于此,便是歧路之羊,愧对天地。书法就像人要会吃饭一样,知识分子必须会写字,对书法没什么特别要求。自王右军开始书法才有一席之地,唐太宗的推崇书法,成为唐代举子应试的内容,出现了一批大家,书体各异,使书法登堂入室。但都是随官声而贵,不是你写的好就一定流传,小民写得再好也只能“泯然与众”,有敦煌经书书法可证。随着唐末书法渐从应试中淡出,特别是到了“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宋代,大力提倡文章第一,书法地位逐渐降低。虽然以后也有大批书家出现,然其自身也只认为是养身怡性的末技,绝不像充满铜臭味的今天被全社会大捧特捧。 若论地位,书法如诗,只能在小众间创造和传播,并非大众普及品。书法的小众命运还是因为书法艺术的先天乏力。学书者必须有文学根底,没有文学的滋养,笔下之字,终难脱俗。与文章相比,书法只是首饰,只能赏玩于文人贵族。文章承载思想,是气,可颐养万物众生。书法也比不上同为艺术品的绘画。绘画的艺术性更丰富和饱满,书法的艺术性只是更隐蔽和单纯。就其习练者中也只闻从画入书有成就的(如启功),未闻从书入画的名人。俗语云“写得好不一定画得好,画得好一定写得好”,可见书法的功力远不如绘画。 书法自然也不是摆设,喜怒哀乐寓于书也是可能的,东洋人就把书法称为书道。真正的书法作品不会是摆设,从内容到形式不可能不表现思想感情。绘画可以表达思想,如悲鸿的奔马;书法也能展示性格,如怀素的狂草。书道其实修炼的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倘若不能受思想领导驱使,只能有益于修身,却无益于社会进步。 思想最可贵,也最娇贵,如同初生的婴儿,稍有摧残便会死亡,非呵护不能生存。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思想自由几无禁忌,诸子直抒胸臆,汪洋恣肆,不用小说来委婉表达,只取《诗经》显示意愿。汉代独尊儒术,宋元明清思想禁锢,人不敢直言,固有戏剧小说诞生,作家藏思想于叙事,夹带私货以求一泄,不如汉唐诗歌大赋。文无思想蕴藏,就成了文字垃圾。如果思想瑰丽,那么小说只是华丽的包装,只有听故事的价值。今人把小说看成最高艺术,实为买椟还珠行为。 绘画起初是直意奔放的,汉画反映的就是人的真实生活。人相为尊,其他为陪衬,贵族平民同上画面,其乐融融。两晋之后仙道释家帝王成为绘画主题,歌功颂德之能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不入画流,张择端也只好把自己的市井画取名“清明上河”。明清思想的禁锢在绘画中反映尤甚,有清一代连八大山人的寒冷山水鸟禽也难寻见,只好寄于花鸟草虫,不敢有所伸展。 古代知识分子自认书法为末技还消磨功夫,盖因专制社会不容思想,沉浸于此,即可成名得利,又可保全微躯,所以书法领域实为古仁人泄洪渠。肉食者对书法亲身示范,旌扬推张,以效法前人为上,把创新视为邪路,非“鄙”实“智”,目的是把知识分子控制在手中。 书法是贵族艺术,真正欣赏的有几人?都是些喜好名利之徒。收买爆炒而沽的成了儒商,悬室正中自得也以雅人自居。品评大伽遍地,一副不值几两碎银的卷轴也被鉴定为百万价级(只是为提取那二成的鉴定费)。评价千万不要多说什么艺术性,点缀几句即可,因为谁内心也不把艺术当回事,只是希望你说成是某某特级特大师之遗作或十万八千年前的孤本就行了。这样一定会被尊为上宾,否则连冷茶也没有。至于“书法显示爱国”云云,则更可笑。近世之汪精卫,宋代之蔡京、秦桧,其书法造诣时人难逾其右,但其行为始终是卖国贼。五千年书法历史中,只有毛爷草书和岳飞的“还我河山”才是洋溢爱国之情的一代书宗。 草木逢春开花,鸟禽遇晴而鸣,都是尽其天职。知识分子当时刻关注群众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粉身碎骨而无怨无悔,此方为国士之风,俯仰无愧于天地。贵族并不是戏剧小说中的花花公子,是上层集团中的有识之士。真正的贵族是爱美人更爱江山,为自己的信仰是绝不缺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殉道精神。 书法可润心,我系小乘佛,有事会成为避世和逃难的场所。凡是不可太执着,不论渡人渡己,修成正果既是大功德。南无阿弥陀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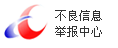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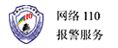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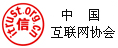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