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失”的侍郎墓 袭普宏 那是发生在“十年动乱”初的事,不知何人所“倡”,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移风易俗”去坟还田的运动在这九百六十万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当时,凡与“旧”沾边的:如带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之“迹”以及经、史、子、集,法帖、古籍、善本、孤本等全部“付之一炬”,古典建筑:如亭、台、楼、阁、御碑、牌坊、家祠、古刹等,“一夜”之间都遭“灭顶”。而名陵、古墓、祖坟、茔林更是与“旧”有联,在劫难逃,为“学大寨”而全面还田,属必“扒”之列,“破立”之后,大多文物古迹“荡”之无存。这,实则是一场历史上的“文化浩劫”。中国几千年很多优秀“文化遗产”由此“断档”,不可“复生”。
山东章丘普集有一个叫“井泉”村子,俗名“井窝头”的小庄,素以“龙泉井池”喷涌,“石衢街坂”溪流,泉水“久旱不涸”而闻名。在其庄西约半华里处的“龙王渠”侧,有一座占地百亩,古柏参天,神道雕像、御碑盘龙,宛如小山般的独冢,叫“毕家林”。是明末礼部侍郎“毕自肃”之墓,在那场运动中也未脱幸免,惨遭“厄运”。而林边所居的毕姓后人,为明末建“林”之初,从淄川王村万家庄西铺“尚书府”中由两户“下人”迁此守墓。至“文革”前,已繁衍达三十口之众,且全部为“毕”姓,时归井泉大队六队所辖。
这是一座“名冢”。之所以有“名”,乃与主人家族、身份及传奇故事有关。墓的主任叫毕自肃,字范九,号冲阳。其父毕木共有八子,分别为自耕、自耘、自慎、自严、自裕、自寅、自强、自肃;八子中,有两人为进士、两人为举人、两人为贡生、两人为秀才,都是“饱读诗书”之士。从所起名字可见其父用心良苦,而其家风“堪正”,个个“出类拔萃”,多有“建树”。肃最幼,自“启蒙”时就聪颖过人,出口不凡、长吐吶正气,十年寒窗,连连中第。1603(万历四十一年)举人,1606(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仕于直隶定兴知县。在任十几年,因该县位于“京畿之道”,迎往、接驾不辞劳苦,扰民“频”生。为此,他誓将“除此陋习、养民于梓”之政推行后,深得民心。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县富而民安,呈“繁荣”象,有口皆碑,当地百姓为其建“生祠”以祝之;1622年毕公以其“勤勉历练”而擢升礼部“主客司主事”,因政绩卓然,被同朝幕僚誉为“神君慈母”,众口一词,无可辩驳。1626年因“边关事急”,肃上书“驭远七事”、“方略九筹”。天子闻其言“至缕”,深称朕意。即擢升为“宁前兵备道参议”、“辽关巡抚”。1628年(崇祯丙寅),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抚宁,领“待郎”衔、属于主战派。在其边关任上,宵衣旰食,夙夜在公,蓄粮备械,买马缮寨,作“封疆”久远计。时因“魏余党”作梗用奸,加之“内帑” 磬,使其缺粮断晌,引起“宁远兵变”。崇祯听信谗言,认其“贪晌”,下旨严查,乱兵趁机入府劫掠。因“家徒四壁、更无余银”,肃不就其辱,于八月初八,在塔山愤然“自绝殒生”。时,经当地“父母”及“仵作”为其剖腹斟验后,尽现“野草败絮”果腹,方知此君“身无长物、清廉如声”。其四兄时任户部尚书,加衔“太子少保”的毕自严三疏叩阍,陈述起由为其鸣怨。将八弟自肃“奏疏”编为{抚辽茶语}、{辽变诸疏}上呈天子。加之当地百姓因“公”忠廉爱国呼之为“青天”并为其上了“万民伞”直达“天听”,尽阐其因,随引起社会奥论“大哗”,此,朝廷方知“社稷衔寃”
待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兵部尚书袁崇焕受命执“尚方剑”斩擒“哗变”首犯十五人,以慰“忠廉”。此,“毕公”已尸骨无存,待魏余党被“尽行根铲”后,崇祯帝明发上谕子以昭雪,并将“东林党”案一并平反。“天子歉疚,旌表忠廉”因无“骸殖”可寻,据说只好用“金头银胳膊”装殓厚葬。天子祭九坛、赐御墓,加封后人。殡后“礼成”之际,其长子于墓前“嚎啕大拗”跪奠曰:“就算是金头银胳膊,也不如俺爹一咳嗽!”
只所以传奇,还有一节与毕府之“渊源”不得不述。清初,毕氏之籍王村西铺与蒲松龄之里洪山蒲家庄都隶属淄川县辖。受毕自肃子侄毕际有之邀,蒲先生受聘毕府“设馆”任塾师,为八位“毕氏”后辈执塾、授业、解惑。塾馆名曰“绰然堂”。“龄”自康熙八年至康熙四十九年“设帐”在此,花甲之年方“撤帐归里”。在毕府三十多年间,因府存万卷书供其“览阅”,又遇“知己”馆东,对“聊客志异”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上的支持。后经毕际有“妻侄”、清初大学士王渔洋力荐,“聊”书幸以付梓。从而使“中国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这部旷世之作得以“问世”!
侍郎墓之所以选中井泉庄为“福地”,因此地位于崔嵬华盖的“东岭山”之阳,墓地头枕溪水长流的“青石龙王渠”,脚登泉水潺潺的“红板云母沟”,活水廻绕,得风得水,却属“宝地”无疑,且墓地距毕府所在的西铺庄不足十华里之遥。 传说已然称奇,但独冢“如山”、“坟田”百亩、御碑“盘龙”、柏萌“蔽日”、巍峨峻拔、御题牌匾、石钟翁肃立两边、赑屃昂首驼碑,使人不得不信。当时,井泉庄动用了百余口劳力,奋战了百日,才将“莹山”移走。“掲棚”后,个个瞠目结舌。然未现“金头银身”,但“墓”修的那叫一个“讲究”。虽为“衣冠之冢”,但穴坑宏大,雕工精细,富丽堂皇,棺木如昨,财宝“满室”。仅“随葬品”就拉了整整十地排车,由民兵押送上交至县里有关部门。但“林”中的御碑、牌坊、神像等石制之材全都碎之铺路。使其御文古迹一夜之间“绝然”,失之不“复”,真乃痛哉、惜哉也!时金价虽“廉”,即如此,也为庄里安电、修路、筑坝、建校、提供了资金支持。然,“侍郎墓”从此消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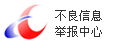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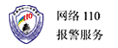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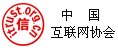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