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历史名碑《廉先生序》石刻,是考证李清照里籍的最好史证。原碑现存章丘博物馆内,复制碑立于清照园正门之东侧,“瓦垄样盖”,周围有大理石护栏,与西侧舒同题写的“一代词宗”碑遥相呼应。据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载:“(石刻)高六尺一寸,宽一尺六寸四分,厚一尺三寸。”正面是序文,题一行,文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序后是李格非的侄子李迥和廉氏后人廉遵谅的跋语,北面是《石阴记》,原残碑除盖石外,其余五块均有文字,尤其以序文残存文字最多。第一次立碑是在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2元)正月,廉复的孙子廉宗师、曾孙廉理等人把李格非所撰序文刻于石立碑祭祖,又请李格非的侄子李迥为碑文写了题记。至元代,“以劫火之故”宋宣和碑仆倒,“圻裂不可植”(清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又由廉氏后人廉锐、廉铎重新镌刻立碑,时值元至正六年(1346)五月。《廉先生序》是李格非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三日为纪念名士廉复所写的文章。大体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廉复弃科举,隐于齐东(即章丘)胡山之麓。第二部分写其隐居期间的行迹和作为。第三部分记廉先生之卒和作序之因。其中关键之句是:“始闻(廉先生)去冬奄已即世”,称“……廉先生为同里人。”末尾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绣江乃源于章丘百脉泉,纳西麻湾水,入小清河,此处绣江当指章丘。李格非的侄子李迥的跋语又从另一个侧面记述了廉坡村的历史,“迥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水静,得先生之居。”据此,也可知李家与廉坡村的地理方位,显然李家是居于明水。后经诸多学者考证:清照故居就在百脉泉南不远处的义仓。一代词宗李清照,曾“词压江南”,其里籍问题历来是研究李清照的一个焦点。早在元朝初期,著名散曲家刘敏中(廉氏后人廉可的表弟)在他所撰《廉先生石阴记》中除极力赞扬了廉复的品行节操外,还高度评价了李格非文章的奇雅瑰丽:“……故阅李之文则见先生之高,观先生则见李文之高,诵其文企乎其人,则见胡山之风神益峻而绣江之波澜而远也。呜乎!……兹石之再刻也,皆知吾乡高人尝有此人,高文尝有此文……。”深为同乡前辈中能有此高人、高文而感到荣耀。由此观之,早在元代,人们就认为李清照里籍、故里就是章丘。到了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当时任章丘知县的河北元城人董复亨,亲自纂修《章丘县志》达三十四卷。特将李格非、李清照的著作,列为重要文章予以全录并作了翔实、中肯的评价。其中有云:“……文叔(李格非)步子瞻(苏轼)之后尘,清照闺阁之秦、黄,敬简称文章之朱、李,名篇大章,光映后先。”又说:“董生曰:余按:《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去处士家才三四里许。”十分肯定地指出了李格非是明水人无疑。清初,章丘著名隐士张光启曾写有《访廉处士故宅》诗,便是史证。在章丘、济南诸多湖泊还建有多处藕神祠,如在大明湖东南岸的汇泉寺里还悬挂有李清照的肖像,可以说清代文人对李清照倾倒备至之极。这时期,李清照里籍“明水说”已完全浮出水面,昭然于世。据清朝道光十三年《章丘县志》卷十六记载:“……阅明水镇西《廉处士》碑李迥跋云:‘少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余,得先生之居’云云,确是明水镇人。”参加编《志》的章丘文人康星焘(字紫垣,号竹林)则无不自豪地在志中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章:“吾里李文叔元佑文学也,其女清照词家大宗。宋南渡后,其艺文散轶,北方罕有传者。即有之率皆仅志其名目然,即文叔《洛阳名园记》一卷,与清照数诗及杂词数阕,已可见其梗概云。”到了民国时期,热心研究李清照的学者有两位值得称道。一位是生于章丘西关高家的教育家、周恩来总理的老师高亦吾。一位是生于明水砚池村的著名教育家、文物鉴赏家管菊人。二人均有李清照研究的专门文章,可惜今已失传。管菊人先生还向当时的冯云和县长提出建李清照纪念馆的建议,殆因战乱频仍,未得实现。现在,两人的夙愿已经实现。现在,两人的夙愿已经实现。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李清照故里的文化设施建设,投资兴建了中国规模最大的李清照纪念馆(清照园)。该园围绕梅花泉而建,楼、台、亭、榭俱全,是一座李清照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被誉为仿宋民居建筑的璀璨明珠。易安居士如有在天之灵,看到今日家乡文化建设之盛景,一定会“荷叶作酒杯,薄醉娇无那”吧!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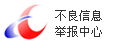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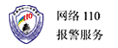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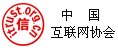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