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酒糟的记忆 美酒——清照百脉泉,产地王白庄,悠悠历史,源远流长。酒怎么出来的,那就要有酒料发酵,蒸馏,勾兑,早年多用地瓜干、高粱、麸皮、稻糠为原料,老百姓习惯叫“王白庄 地瓜干子酒”。 酒糟是出酒后的下脚料,老百姓都叫糟糠。五六十年代,是个缺粮的时代,老百姓粗粮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猪哦,于是糟糠成了喂猪的主食,酒糟糠皮里有零星粮食成分,含有酒的气味,猪爱吃,吃饱就睡觉。 酒厂车间一个周期下来,才出酒糟,数量不多,积攒到一定数量,开始对外卖。往往是王白庄亲戚熟人告知那天要卖糟糠了,周边村庄的都去排队挨号买糟糠了,那时候没有垄断,倒卖一说,排上的,都可以分到几小筐,价格也就块吧钱。 五几年,我刚上小学,独轮车的两把都够不着,只能一只手握车把,一只手抓肩带绳子,八九岁就练就了一手推独轮车的“技艺”,奶奶给牵扶着,跟头咕噜地跑几里路。 为了能抢到号,半夜就去酒厂门口排队,必须按小车计号,人排队不算,天亮了,黑麻子老头终于出来了,都亲切地喊他姜大爷,抢着递烟,他手一摆,不接,都要规规矩矩地排好队,他才发票,10个小车一组,选好组长。他根据糟糠的数量,发多少组的票,每次也就10张不到,后面的回家不让等了,下次再来。能排上的那是喜洋洋,赶紧凑钱,挨不上的只能空车走了。 八点开门放人,热气腾腾的酒糟堆前,都羡慕地看着第一组开始装筐了,那筐特殊地大,高三尺,宽二尺,长六尺,两边是抬架的木棍,木头做的大锨,规定只能举高了使劲往下砸,但木锨不能拍打,黑麻子叼根烟,盯得死死的,拍了,给一脚晃下去,再搞说不定废除你这个组的资格,让你等到最后了,所以都不敢造次。 装筐要有气力举起用力往下猛砸,这样实在,多出不少,尤其是筐满了,超高冒尖,那就是学问技术了,先边上砸,技术高的能超出筐边,一点点往上凑,直到再也驮不住了,慢慢收尖,心急求多,往往塌下了一边,弄巧成拙,再也装不上, 白费劲了,麻子说好了,只有抬走,下一组了。傍边看也长学问呢,都摩拳擦掌,琢磨着咋能多装几锨。 10人一组,都不愿意女人老人小孩多,掌锨没有力气,往往在排号时,精神的就开始使心眼了,故意退出,等男劳力的群组合,起码要有两个壮劳力才行,妇女孩子多的拿不动那大木锨哦,架筐可以围一圈小心翼翼架出来。后来形成了一个规矩,商定装筐的俩人多给一份,也是合情合理的,多装几锨就有了,都没有意见。一次挨上几个婶子大娘一组,小孩多,没有法子哦,只好上阵了,的确是不行,十几锨下来就气喘吁吁了,还是等的两个大爷大叔,帮助装满,他们也想快一点装筐,让我们一帮孩子好生感激,那时候还没有出雷锋,老百姓叫“行好”! 倒筐分堆,女人孩子就麻利了,先扒成小堆,再手捧匀和,大小没有意见了,就挨个装袋子了,放小车高高兴兴推出酒厂大门,到家也都过午了。为什么非要按小车排号呢,很简单,那时候家家也就一辆小独轮车,顶多你能再借一辆,如果按人排号,两三人一站,就会挤占号了,酒厂也属于人性化吧,不允许投机取巧。 奶奶每次要给我点小奖励,从卖肴菜的小车花2分钱买包咸菜,让就窝头煎饼吃早饭(半夜就出来排队哦),高兴还会花一毛钱买条小炸鱼,那是最香美的早饭了。 等的时间,我们会跑到车间看机器,锅炉,一片蒸汽,工人光背穿裤衩,大汗淋漓地搅拌,出渣,拉车快跑,边呵斥我们让路!那时候没有电,摇把水车供水。 推糟糠的记忆尤深,至今还能回味那酒糟香醇的味道,现在都讲究什么浆香型,醇香型,佳酿,其实酒糟里的味道全都有了,再好的酒,不都是里面浸透发酵蒸馏出来的吗? 赞美清照百脉泉,王白庄酒,糟糠也曾是珍宝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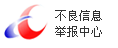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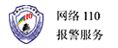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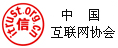
![]()
![]()
![]()
![]()
![]()
![]()
![]()
![]()